注:本文所有“中医”,其涵义均是指“中国传统(古代)医学”,与之对应的概念是“西方传统(古代)医学”。“现代医学”不存在中、西分野。
关于“中国传统医学”,亦即中医,中文知识界有一种相当常见的说辞,大意如下:
“阴阳五行理论已经过时,但中医是经验的医学,从神农尝百草至今,中医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成果,中医药是内容丰富、价值无可估量的宝库。”
进而,很多人主张“废医验药”。
“废医验药”是很好的主张。遗憾的是,验药的结果,却让“几千年经验的积累”有些措手不及。
“验药”的惨淡往事
当代医学史上,有过两次针对中医的大规模“验药”。
第一次始于1958年。
此次验药运动覆盖全国,手段是对传统中药做药理实验,目的是筛选出其中的有效者并寻找新药。
到了1961年,在“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”上,参与验药的中医界人士无奈承认:
“阴性结果较多,肯定结果较少。不少(宣称)临床报告有效的方药,在动物实验中得不到证实。”
“我们单位所做的中药筛选工作多数为阴性结果(注:不能证明有效),少数为阳性结果。”
“用观察血管脆性、血凝时间等方法来研究止血的中药,结果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……”①
不过,与会的中医界人士拒绝将“得不到实验的证实”,等同于“中药本身无效”。
在会上,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来解释为何“多数为阴性结果”——或辩称“有的是由于对中医学习还不够,有的则是由于对待科学工作的严肃性不够”,或辩称“过去方法上不够多样化,因此大多数是阴性结果”;且集中火力抨击了现代医学的“验药”方式不适合中药,宣称:“中医理论很多是西医难以理解的,……目前的一些实验方法很难反映出中药的真实药理作用。”②
他们强烈主张,用“临床疗效”取代“动物实验”和“双盲实验”,作为判定中医药方是否有效的依据——事实上,当时的中药筛选正是这样做的,许多中医机构乐衷于用“临床疗效”取代“动物实验”和“双盲实验”,来判断某一药方是否有效。结果就是,这些宣称具备“临床有效”的药方,大多数很难得到“动物实验”和“双盲试验”的证实。正如《中医杂志》1963年的一篇学术论文所承认的那般:“结果的可重复性不高以及与临床结果的不一致,是中药药理研究中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。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1959年抗癌中药的筛选报告指出,初试有64种药物对癌细胞的抑制率>50%,……但经复试,凡是能够评价的结果,竟没有一次得到>50%的抑制率,即使抑制率达30~49%的,也只有13药次;湖北省卫生防疫站1958年报告,48种中药中,只有黄连对流感病毒呈抑制作用,但西安方面同样筛选(1959),曾多次购置黄连,都未能重复出黄连对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,与此相反,与湖北方面重复的16种单味药中,却至少有12种对流感病毒具有抑制作用……”③
众所周知,不能通过“动物实验”和“双盲实验”,结果不具备可重复性,这种所谓的“临床疗效”,往往属于幻像——比如患者的好转实际上属于自愈,而非药物起了效果。
在1961年的会议上,针对某些中医界人士以“中医是一种临床医学”为由否定“动物实验”“双盲实验”的论调,有医学工作者直接了当驳斥道:“在评定中医药(临床)疗效时应实事求是。有时由于未掌握疾病的规律,把自然好转的病人误认为是药物的疗效,也是应该避免的。如果某药能治好一例结核性脑膜炎尚可理解。但是如果说某药能治好腮腺炎(笔者注:该病绝大多数可自愈),如无客观可靠的指标,就很难肯定。仅根据病人主观症状好转就认为有效,根据是不足的。在大多数情况下,必需有适当的对照才能判断药物的疗效。”④
![图片[1]-不要被「几千年经验的积累」这种话迷惑-网络宝藏](https://wangluobaozang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7/image-37.png)
图:1961年首届药理学会论文集
第二次全国范围的“验药”,始于1971年。
据吴新生《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》一书披露,此番验药运动的缘起是:“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,……当年(1970)11月份,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,由卫生部牵头向全国医疗系统发出号召,展开攻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科研攻关活动。”⑤
如此自不难想象这场验药运动的规模。
此次筛选,采取了“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的方式。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1975年,全国共派出医务人员近30万名,临床验药治疗440多万病例。
但结果同样令人遗憾。中医陆广莘无奈承认:
“1971年全国范围的筛选慢性气管炎中药,针对‘咳、喘、痰、炎’,筛选出止咳、定喘、化痰、消炎的18种草药,却又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。百余年来,从麻黄素开始,能从中药里成功提取分离成为化学药的不到60种。”⑥
尽管当时的许多中医界人士,再度将原因归咎于“实验方法”和“疗效设计”,继续强调“中西医学观存在差异”。但验药结果相当惨淡,终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。
于是,问题就来了:为什么明明有“几千年经验的积累”,到了“验药”环节,却难以得到期望中的丰硕成果,反而是“阴性结果较多,肯定结果较少”“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”“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”?
有效积累与无效积累
答案其实很简单。
“几千年”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,确实容易给人一种“最终积累”一定特别厉害的错觉。殊不知,经验的有效积累,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:
(1)“经验”的真实性可以被检验。
(2)“经验积累”的渠道非常通畅。
遗憾的是,在漫长的“几千年”里,这两个前提并不具备。这直接导致中国传统医学的经验积累,长期处于一种非常低效的状态。
再具体一点解释就是:
(1)一种“治疗经验”,要被证明有效,首先需要大量的临床病例;然后还需要通过“双盲实验”一类的办法,排除掉其他因素的干扰,尤其是排除主观偏差。
比如,《三国志》记载,华佗曾凭借用手摸孕妇腹部,“(胎儿)在左则男,在右则女”的经验,准确诊断出孕妇怀了男孩——这是典型的以偶然为必然、存在主观偏差的“伪经验”。
《三国志》还记载,张角、张修用“符水”给人治病,治好了就是“符水”的效果,治不好就说病人的心不虔诚,“不信道”——这也是典型的未排除自愈因素干扰、存在主观偏差的“伪经验”。⑦
(2)一种“有效的治疗经验”,要被有效积累,首先需要作为知识沉淀下来,在刀笔时代,沉淀的方式自然是写成文字载入典籍;然后这些文字典籍,还需要有传播渠道,在传播渠道的末端,必须经得起重复验证。这些,必须依赖“学术共同体”才能做到。
很遗憾,在近代大学和学术期刊制度建立之前,中国传统医学不存在“学术共同体”。
所以,在中国古代,某位民间医生发现了针对某种疾病有效的药物——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,民间医生既无法获得足量的临床机会,也没有进行双盲实验的意识,自然也就无力确认药物的有效性,《本草纲目》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等,就是这方面的典型,对绝大多数前人留下的药方,李时珍等传统医学工作者只能抄录,无法甄别,以至于上吊绳治癫狂、吃白云治哑症这样的药方比比皆是。⑧——然后将之写成文字,变成知识有效传承下来,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
史实也可以证明了这一点。那些站在最顶端的民间医生,比如华佗,都没有能够将他们的有效药方传承下来,留在史书中的,只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传说,比如断言某某与妻子行房必死、某某五日必死、某某阳寿只有十年……普通民间医生,情况自然更糟。
在民间不存在任何“学术共同体”的古代中国,稍稍能够做到“有效积累”的,其实只有官办医疗机构。
比如,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写成后即面临失传的困境,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收集了一些残章,将之部分保存了下来;今天所见的通行本,则是宋代官办的“校正医书局”校订整理的版本。
然而,官办医疗机构本质上仍属于衙门,不是“学术共同体”,他们对医疗经验的“有效积累”,也很低效。
以御医为例。对他们而言,伴君如伴虎,“独到见解”实际上常常等同于自招祸端,为了趋利避害,他们在诊治时常常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,乐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治病之药;乐衷于用“慢治”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;乐衷于从众诊断随大流,寄望于法不责众……如此种种,是历代御医们最核心的“专业技术”。
当然,皇室也不是傻子。清代民间医生杜钟骏被召入宫给光绪帝看病,发现当时共有6名医生轮流给光绪看病,分别诊断、分别开药,医生之间不许互通讯息。这种规矩,很明显是想要防范御医为求自保“从众诊断”。
但这样做的结果,却是“千人千方”——传统医学缺乏“动物实验”“双盲实验”这种学术规范,药效的判定标准相当混乱(比如不能区分自愈与药愈,也不能区分究竟是哪一种药物是有效成分),于是乎,最终的用药决策权往往只能归于“圣裁”。比如,慈禧曾将两张供自己服用的药方——民间医生马文植所开与太医院所开,“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”,让朝中大臣来判断该用哪一张;大臣们自然不敢担责,只好回复称“臣等不明医药,未敢擅定,恭请圣裁”,仍请慈禧自己决定;于是,慈禧决定仍用太医院的药方,同时又命“马文植主稿”,可谓和得一手好稀泥。⑨
这种“难以有效积累”,有一个众所皆知的典型案例,那就是青蒿素(某些文献或称青蒿,或称黄花蒿)在中国古代的发现、失传,以及在中国当代的重新发现。
东晋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中,已记载有“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”,可以治“寒热诸疟”。《肘后备急方》是历代官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必备典籍,但自东晋至晚清,这种治疗疟疾的有效经验,并未获得真正的重视——主要原因在于未获得重复验证、未能找到其中的有效成分(比如在使用方法上出现了问题);而不能得到重复验证的原因,又在于官办医疗机构不是研究机构,在积累上非常低效——所以“青蒿可治疟疾”的记载,虽然留存在典籍中,却始终没有能够变成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。直到20世纪60~70年代,依赖现代医学的实验体系,青蒿素才获得了被“重新发现”的契机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不但中国传统(古代)医学“几千年经验的积累”非常低效,西方传统(古代)医学“几千年的积累”也同样如此。
比如,“十七世纪德国药典有五、六千种药物,今天继承下来的只有少数。”(药理学家金荫昌语)
再比如,在“产褥热”这个问题上,中国与欧洲的传统医学,都长期深陷在错误的“恶露抑制”理论当中,认为孕妇之所以在产后出现发热症状、进而导致死亡,是因为她们在怀孕期间,血液中积累了大量污物毒素,需借助排出恶露来清除,冷空气进入子宫、身体受冷、饮用冷水、受到恐惧惊吓等,都会导致子宫内血管出口关闭,使恶露难以排出。进而,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,产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“坐月子禁忌”——房间必须被关得密不透风、产妇不能下地必须卧床、多少天内不能碰凉水、不能洗澡……
直到19世纪中叶,欧洲的近代医院走向正规,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医生、匈牙利人塞麦尔维斯(Ignaz Philip Semmelweis)才获得机会发现,“感染”(具体感染了什么,他当时还不清楚)才是产妇患上产褥热的根源;稍后,法国科学家巴斯德(LouisPasteur)和德国医生科霍(Rober koch)相继发现细菌,塞麦尔维斯关于产褥热的发现,才被欧洲的“医学共同体”所承认,变成一种被有效传承下来的“医疗经验”。⑩斯
说了这么多,归结起来,其实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:
面对“××是几千年经验的积累”这类话时,必须要心存警惕,必须注意逻辑链条的完整,多问几句句:这“积累”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?是有效积累,还是无效积累?是高效积累,还是低效积累?
毕竟,真理可以在“几千年”里始终尘埋,谬误也可以在“几千年”里恒久流传。真正重要的,不是“几千年积累”,而是能否做到“有效积累”。
(完)
注释
①中国生理科学会药专业秘书组/编著,《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: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专集》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62,第161、167、172页。
②同上,第168、171、172页。
③高晓山,《建国以来我国中药药理研究概况》,《中医杂志》1963年第8期。
④《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: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专集》,第168页。
⑤吴新生等/著,《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5,第372~375页。
⑥陆广莘,《中医学之道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1,第301页。
⑦《三国志.方技传》《三国志.张鲁传》。
⑧隋风,《上吊绳治癫狂,吃白云治哑症,<本草纲目>们不可轻信》,短史记2018年9月19日。
⑨恽丽梅:《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2010年,第86、83页。
⑩言九林,《“欧美人不坐月子,是因为体质与中国人不同”之说,相当荒唐》,短史记2018年11月4日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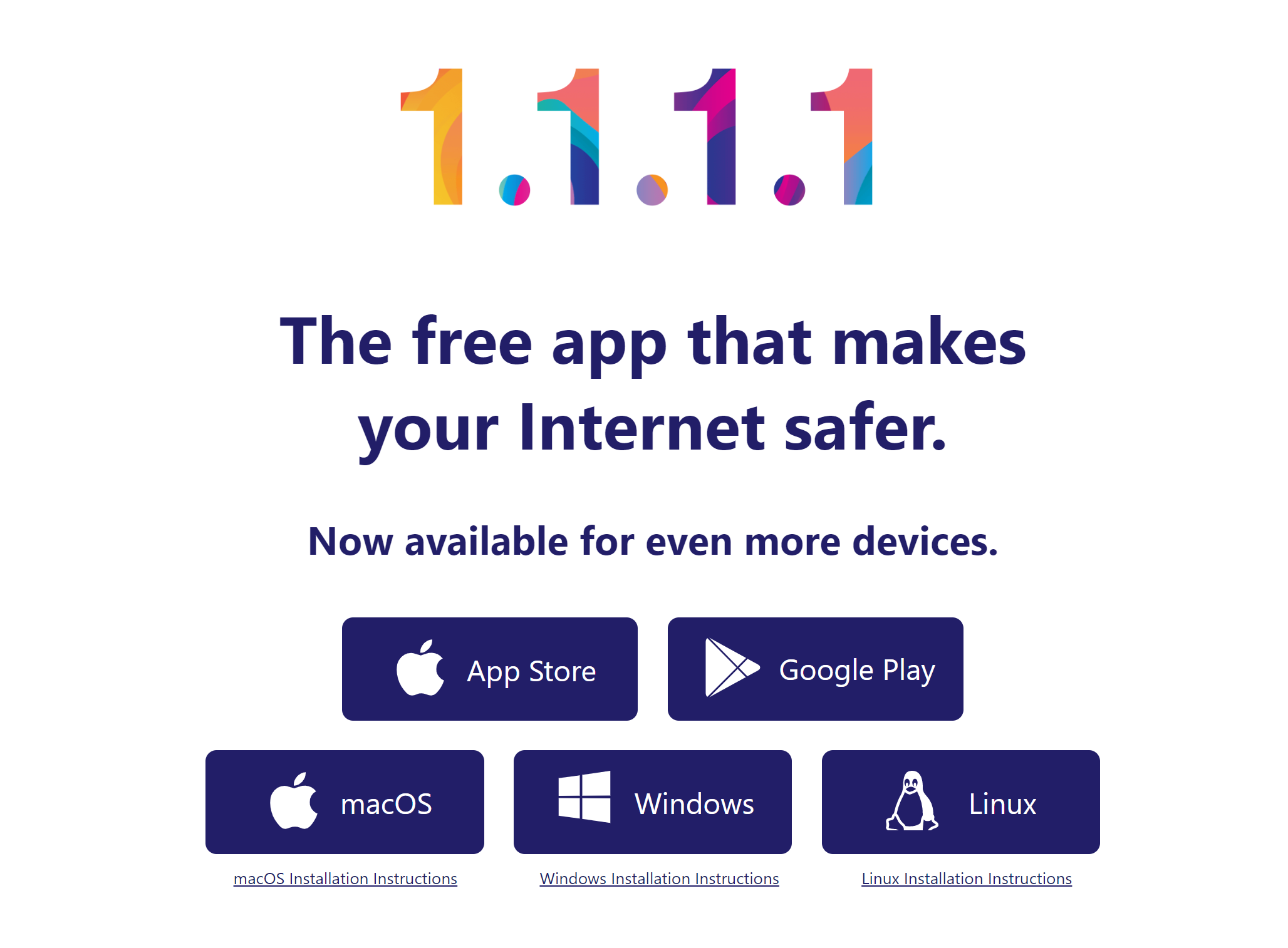



暂无评论内容